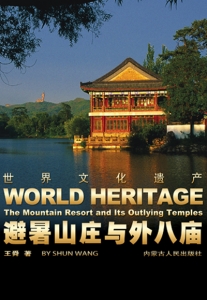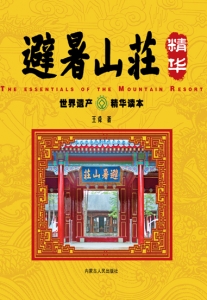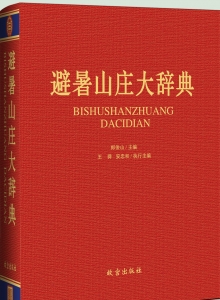八
整整一宿,孙立本基本没睡:天亮以后两拨人,黄小菊和包书记,来了咋办?思来想去也没弄明白。再听楼道里,韩大平的呼噜跟肥猪一般隔着好几道门都传过来;赵小凤夜猫子这一夜电话就没断,又哭又笑闹鬼似的。孙立本暗道真得佩服这些乡镇干部,人家这俩下子都是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摸爬滾打多少年练就的,可不是谁来个两三个月就能学到。
早上起来孙立本就叫他俩,韩大平快,一听敲门揉着眼就出来,他好像也没刷牙洗脸的习惯。赵小凤不行,且在屋里打扮呢。韩大平在楼道喊又不是让你上花轿,美什么美。赵小凤喊我不收拾怕把孙镇长吓着。孙立本说:“包书记是那么说,可光吃炸酱面行吗?”
韩大平说:“我看不行呗。咱得做两手准备。心情不好,就吃炸酱面。心情好,就吃‘一朵红梅’。最好留下,晚上再吃‘白云深处’。”
赵小凤脸上稍显白就出来,下身还穿着睡裤。
孙立本说:“别光顾上边忘了下边。”
赵小凤乐了:“这就对了,别一天到晚皱个眉头,死的活不了,活的还得逗。”
韩大平说:“人家从来就顾头不顾腚,这还穿着,不赖了。”
赵小凤瞪他一眼说:“我出来是告?你们,得赶紧先去‘一朵红梅’,不然万一包书记提前来了,她也来了,不是搅局吗?”
韩大平点头说:“太对了,我去,就按咱们昨天商量那个数儿,先稳住她。”
孙立本多了个心眼说:“还是我去吧。”
韩大平说:“你去,可别说姓韩。”
孙立本说:“自摸,让她姓梁。”
赵小凤说:“还是让孙镇长去吧,顺便让她准备中午饭。老韩你安排伙房炸酱面。”
韩大平问:“那你干啥?那早饭呢?”
赵小凤说:“没眼色,我这妆才上一遍,还有两层呢。书记来,弟妹来,我得打扮得漂漂亮亮闪亮登场。早饭不吃了,减肥!”转身回去。
孙立本也顾不上吃早饭,下楼就奔了“一朵红梅”。这大汤泉之所以叫大汤泉,简单说就是有温泉,过去清朝康熙皇帝来塞北围猎,在这洗过,也叫洗汤,还留下诗句。解放后一会儿忙革命一会儿忙生产的,谁还有时间到这来涮巴。不过,这里也没浪费,县里在这建了荣军疗养院,后来改革开放,先是外地人发现这可是块宝地,问这热水都流哪去了,说引沟里放凉了浇菜地,大罗卜长得好。把人家心疼的不行,立刻就过来建饭店旅馆,生意红火,当地人这才意识到守着金碗要饭吃,赶紧自己干。但也不是可地都有泉,烂西瓜打个眼儿就冒汤儿,那就看谁家家址有旧泉眼或在热水地脉上。梁红玉家就在老泉眼上,又临街,因此,“一朵红梅”早先生意一直挺好的。但真是架不住连镇政府带其他部门一些个人这些年的猛吃,把她吃得快坚持不住了。不论是做生意还是过日子,往里进钱和往外出钱,一进一出,既便是小钱,时间一长,就大不一样了。
太阳刚刚升起来,天地洁净得如清水洗过。镇子的大街上喧闹异常,这是每天商品交易的重头戏之一——早市。原先早市只有当地农民卖自家产的蔬菜,后来就发展到与集市一般,什么都卖,不光本地人,远处的都开车来。孙立本毕竟是搞宣传出身,还写过诗歌,一看这场景,不由地就想要吟上几句,可还没吟出一句,就有人用脚碰了他一下说:“没长眼睛呀,没看我双手都占着。还不帮我一下。”
孙立本侧脸一瞅,巧了,是梁红玉。还真不是胡夸乱赞,深山出俊鸟,这梁红玉长得真是绝了。乌发如缎小脸精致腰身苗条,孙立本心里说这要是唱戏扮上,比南宋的梁红玉还梁红玉呀!也难怪她的店要给吃黄,哪里去吃饭,恐怕多是为看她这小模样吧。什么叫秀色可餐,这就是。可能心里还有夜里俩人喝酒的热乎劲,梁红玉挺不见外,孙立本也没避嫌问:“我帮你啥?”
梁红玉柳眉含笑,小声说:“帮我掏钱,快点,四十。”她两手各拎一塑料袋东西,前面一个卖鱼的摊儿围着不少人,都在抢挺新鲜的川丁子。川丁子是小鱼,炸着吃好吃,一般饭馆都少不了这道菜。孙立本一看她真是腾不出手,就问在哪,梁红玉头一歪胯骨一翘:右侧裤口袋。孙立本伸手去掏,手一下去,呀!不对,没钱,这是啥?抓两把,溜滑、温润、挺拔,哎喲!梁红玉抿着小嘴说:“抓啥呀,好痒,那是我大腿。”
天哪!孙立本触电似的收回手。他也算反应极快了,就势抽出右手抓过梁红玉手中的塑料袋,左手掏出自已那张五十元的票子,递给卖鱼的,说:“走走,我正要上你那去。”
梁红玉挺乖的就跟他走。还好,生意兴隆,买的卖的都在注意这个细节。不过,这已经把孙立本弄得心惊肉跳,他边走边说:“我说,你这可不好……”
“不好?不好你抓起没完?”
“就两下。你口袋怎么是漏的?”
“偏开口的,你伸错层了。”
“那也得穿内裤。”.
“我光身子睡惯了,今早一着急,忘了。”
迎面过来俩岁数稍大的妇女,显然没见过孙立本,瞅了两眼,就拉住梁红玉一个笑道:“好呀你红玉,还暪着我们!啥时请我们喝酒……”
梁红玉略一愣立刻说:“还没定呢,你们看行不?”
另一个说:“嗯,不错,看着还行,就是个不高,干啥的?”
梁红玉咯咯笑道:“做大买卖的,大汤泉最大的老板!”
另一个问:“你的买卖是那家?”
孙立本索性也胡扯了:“公家。”
俩人又往前走,孙立本狠狠瞪梁红玉一眼,却见她流了泪。就问:“你哭啥?我够配合的啦。”
梁红玉说:“我幸福。”
孙立本说:“你、你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到了“一朵红梅”,三层小楼一楼是餐厅,里面有五、六位岁数挺大挺大的老人正在吃饭,有大白馒头、粥,还有白菜豆腐等,热气腾腾。孙立本奇怪,怎么穿得都这么整齐而且颜色式样相同。梁红玉说荣军疗养院就剩下这么几位了,伙食一般,我每天早上请他们吃一顿。过些时我后面的房子建成,就把他们都接过来彻底在这了。孙立本心里忽悠颤了一下,没想到这个梁红玉,还挺有爱心的。就问:“给养老?”
“养呗。这都是功臣。”
“费用呢?”
“有我吃的,就饿不着他们。”
进了里屋,孙立本赶紧说:“我来就是告诉你,镇里欠你的钱,分两次还清。”他把三分之一变百分之五十。
梁红玉转过身,死死盯住孙立本说:“今天我要是有福,就留住你。”
孙立本说:“今天你要是有福,就放过我。我还有件事,今天我要是有福,等我媳妇见到你,你千万别说肚子里姓孙。”
梁红玉笑了:“那姓什么?”
孙立本说:“姓什么我管不着,反正不姓孙。”
梁红玉低声说:“我看你呀,老实人一个,还是别在这干了,这里不是做文章人待的地方。实话告诉你,其实啥都不姓,我肚里也没孩子。”
孙立本说:“那、那你干啥糟践自己。”
梁红玉说:“没了男人,我咋办,干等着挨欺负?”
孙立本说:“我看你净欺负人来着,你把小马的脖子都挠了。”
梁红玉说:“我后院又盖房子,缺钱,一急,撞了一下,可没正经挠,要挠就挠脸了。”
孙立本说:“往后,火气还是别太大,好日子长着呢。”
梁红玉被感动:“听您的。这么着,您是好人,肯定升大官,在大汤泉,只要待一天,这就是你的家,您随时来。”
孙立本说:“我还敢来?我都为你弄得快没家了。”
梁红玉说:“没家正好,我接着。”
孙立本拔腿就要走,说:“小马有你账号,你就抓紧盖房吧,那几位老人,镇里一定帮你,要钱有钱要物有物。”
梁红玉说:“你一定来。都现成的。不来我去找你,想不来也不行!”
孙立本瞅瞅四下,就那几位老人,他双手抱拳说:“梁将军,红玉娘子,求你啦,放我回北国吧,我是金兀术还不行吗!”
梁红玉乐的蹦高:“那、那你答应我个条件。”
孙立本问:“啥条件?”
梁红玉说:“你亲我一下。”
孙立本蹦起來,说:“真想亲,有规定,不敢亲呀!”转身就跑。
九
回到镇里才进厕所,就听大门外有汽车声,孙立本心想小马回来了,没准黄小菊也来了。既然工作做的及时,梁红玉那里不必担心,所以,不妨沉住气。随即就听门响车进院,果然小马喊:“孙镇长,嫂夫人到了。”孙立本心说喊什么喊,一紧张,越想尿越尿不出来,坏啦,看来真是前列腺有毛病了。
院里又有了赵小凤的声音:“这是嫂子吧,真漂亮!这位是……哎哟,张敏?是您吗?你咋这样了?”
马上就有女人哭着说:“老白他……天呀!这可叫我们娘俩怎么活呀………”
韩大平说:“小马,快去找镇长。”
小马说:“门卫说进院啦。”
赵小凤说:“我知道,准在厕所里,他这些天跟茅坑有缘。”
孙立本索性不尿了,窜出来说刚进去没一小会儿。然后看见黄小菊,还有一个女的比黄小菊还年轻,从大轮廓一扫,绝对美女,只是两眼红桃子一般,也没打扮。上前一问,是白顺成的爱人叫张敏,是市文化馆的,黄小菊的好朋友。孙立本心想这个黄小菊可真够二的,你自己来还不够,又带这么一位来,这可怎么接待呀?一会儿包书记还要来,娶媳妇发丧放炮打幡,怎么全往一块上凑……
这老些人,咋也不能苞米秸在院里戳着,就得上楼进办公室。看來黄小菊早有准备,让张敏去赵小凤办公室,自己跟着孙立本,一进屋就把门碰上,用背一靠,谁也别想进。孙立本一看这架式,忙说:“咱有话好好说,这可不是在家里,传出去影响不好。”
黄小菊说:“你放心,那个叫什么梁红玉的肚里的孩子姓孙姓猪姓沙都行………”
孙立本说:“怎么还出来朱沙了?”
黄小菊说:“再加个姓唐的,正好你们师徒四人嘛!”
孙立本乐了:“是小马路上说的吧?不信,咱这就去对质,人家肚子里根本就没怀上,她是为了要账。”
黄小菊说:“那事先放一边儿,我问你白书记在时跟你关系怎么样?”
孙立本明知故问:“白书记?哪个白书记?”
黄小菊说:“还有哪个白书记?就是张敏她男的!”
孙立本说:“是他呀。哎呀,我说黄小菊同志,你可要讲政治呀。这个白顺成眼下虽然还没有明确犯了什么错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已经不再是中共大汤泉镇的党委书记了,故此,你再那么称呼是不准确的……”
黄小菊有点急:“行行,你现在是一把手,我是说,姓白的出事了,对她爱人、张敏,按政策,大概……也不该……当成有错误的人看待吧?这话说得怎么这么绕呢,都是你给我绕的。”
孙立本说:“那得看她参与没有。从已经报道的案子看,好多贪官都是夫妇一同做案的。张敏今天来,如果想交待这方面的事,很好,但她男人的案子是市直里直接抓的,我想她住在市里,还是不要舍近求远……”
黄小菊抓起桌上的报紙就砸过来:“孙立本!你、你要气死我呀!你想绕哪里去?今天我陪张敏来,是她要进她男的姓白的办公室收拾收拾东西,就这事!别的少说!”
孙立本抱着报纸说:“早说呀,白顺成的办公室?我们没钥匙。”
黄小菊说:“她有。”
孙立本说:“她有?她有也不能开吧。”
这时,外面有人轻轻撞了一下门,又听小马在楼道大声说:“白书记这门的钥匙,我看这几把都不像呀!”
孙立本心说坏啦,一把推开黄小菊,开门一瞅,白顺成的办公室门外,赵小凤站后边,张敏正拿着几把钥匙一把一把试。孙立本喊:“停停!这门可不能开呀!”
赵小凤说:“就当着咱的面收拾点衣服什么的。”
孙立本说:“那也不行。”
赵小凤说:“那这房子早晚不能腾出来你搬进去?”
孙立本指着楼外说:“我、我上厕所办公,也不进这屋!”
张敏呜呜哭道:“小菊呀,他、他怎么这么凶呀!我听我家老白说,他俩关系挺好的,他能当镇长,还是老白同意的。这叫去谈话才几天呀,怎么就变成这样?我是没法活了!”
黄小菊喊:“孙立本,你、你也太不给我面子啦!”
孙立本就势用身子挡住门:“别的都行,这面子不行!”
黄小菊伸手就抓就挠,赵小凤明白过来,紧忙抱住黄小菊,小马也上前连劝带推,把黄小菊和张敏引进孙立本办公室又关上门。楼道里剩下孙立本和赵小凤,韩大平匆匆上楼来问:“咋啦?吵吵巴火的,咋还打起来了?”
赵小凤说:“张敏要进老白的办公室,我觉得纪检都查过去,没事吧?”
韩大平眼珠都瞪圆说:“你、你不是小凤,你是二缝儿,你二X呀!这事你怎么敢答应!”
赵小凤说:“多亏老孙给拦住了。是是,这事是不合适,可总觉得过去关系挺不错的,这会儿又怪可怜。”
孙立本说:“她还要开咋办?”
韩大平掏出火柴盒,拿出两根火柴就往锁眼里一插到底,再折断:“这回,万能钥匙都开不开。”
赵小凤说:“将来呢?”
孙立本说:“換新的呗。你去做工作,把她俩劝走。”
赵小凤说:“行,将功折过,你俩躲起来,看我的。”
老天爷!一说就是两个来钟头,都快晌午了,楼上的人还不下来。孙立本躲在伙房闻着炸酱的香味,跟韩大平说:“我早上没吃饭,要不先给我吃点什么。”
韩大平说:“都啥时候了你还想吃,心倒是挺宽呀。”
孙立本说:“那就忍着。”
都过十二点了,赵小凤才跌跌撞撞地从楼上下来,脸上的妆全完了,都是汗道子。随后小菊小马架着张敏,都要上车了,孙立本有些不忍,鬼使神差的跑出去说:“你们、你们吃了饭再走吧。”
黄小菊说:“你躲哪去啦!好,那就吃了饭走!”
赵小凤差点蹦起来。可气死她了,累得口干舌燥,好容易答应走了,你又冒出来瞎客气!那好,她说:“那就去伙房吧,有炸酱面。”
孙立本说:“不行,伙房,我有客人。”
黄小菊说:“我们也是客人。”
孙立本说:“别别。小菊,你不是要核实那个女老板怀孕的事吗?你们去‘一朵红梅’。”
黄小菊说:“是那个梁红玉吧?我去会会她!”
孙立本说:“她那的菜又便宜又好,可劲点。”
黄小菊说:“我点鲍鱼。”
孙立本说:“她只有川丁子。”
黄小菊说:“不可能,人家有什么菜你怎么会知道?”
孙立本说:“咋着,你还不信?”
黄小菊说:“我就不信!”
孙立本说:“不信?一大早是我和她去一块儿买的!”还行,没把她连内裤都没顾上穿说出来。又说:“不信你们去,有鲍鱼,我大头朝下走。”
黄小菊说:“有孩子呢?”
孙立本说:“我从十六楼跳下去!”
小马有眼力价,好说歹说把小菊她俩劝上车开走了。赵小凤乐了:“你可真行,什么都知道。连梁红玉穿什么色的内裤都知道吧。”
孙立本说:“我就是什么都知道,还知道你们还有养亷股!”
赵小凤问:“什么股?”
孙立本说:“别装傻,养亷股!”
韩大平说:“这个我知道,那是以前县里给各乡镇一把手设的,都拿些钱,由上面统一使用、分红,咱大汤泉就白顺成有,后来不敢弄了,现在没了。”
赵小凤说:“好家伙,罗卜快了不洗泥,赶上‘屁股’谁都有了。老孙,你这可不行呀,这会儿你都变成纪检委了,我尿都吓出来了。”
孙立本看他俩那样不像是装的,忙说:“谁叫你说我连内裤颜色都知道。那个什么,这包书记咋还不到呀,我都饿透气了。”
韩大平说:“那会儿小钱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他说他不想等了,他要走了。”
孙立本问:“要走了,啥意思?”
韩大平说:“回县城吧。闹半天还是挨个乡镇跑呀,啥重要的事,至于书记这么亲自出马。”
赵小凤说:“我看不是什么好事,起码不是公事。”
韩大平点点头说:“有道理,发通知有电话,开会有视频,哪有书记自己跑的。”
孙立本不想瞎猜了说:“炸酱别太咸了,咱们那大师傅原先是卖盐的吧。”
赵小凤说:“是卖酱的。”
三个人乐了,说些闲话等着,后来弄了个凉馒头分吃了。下午三点了,小马回来了,问:“还没来?我这边可都弄妥啦,正好有熟人去县里,顺便把她俩拉走了。”
孙立本说:“有鲍鱼了吗?”
小马说:有杏鲍菇,还有炖柴鸡,挺好的。”
赵小凤说:“张敏还哭吗?”
小马说:“哭什么哭,她俩后来商量,要是老白判十年以下,就等。要是十年以上,就离婚,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
孙立本问:“她们临走还说啥了?”
小马说:“张敏说一旦让开门了,告诉她,她还来。”
赵小凤问:“孙镇长爱人说啥?”
小马说:“说这事没完,回去再跟算账。”
赵小凤拍手乐道:“得了,回家跪搓板吧。”
孙立本装做很不在乎地说:“我跪?还不定谁跪!现在都用洗衣机,哪来的搓板。”
小马的手机响了,他听了一阵,脸色大变,连说这就去这就去。装起手机,他说:“小钱上吊了,在乡里。”
韩大平问:“死啦?”
小马说:“说舌头都出来了,拉县医院抢救去了。”
韩大平说:“哎呀!那会儿他跟我说他要走了,是这个意思,我咋没听出来呢!他哥跟我还是老校友呢,小马,你快去吧。”
孙立本说:“咱们去不?”
赵小凤说:“你也二了吧,你知道他为啥上吊?这关键时候,没有县里电话,咱不可贸然行动。”
孙立本连连点头说:“说得对,小马你快去吧,用情况通电话。”
小马车还没出院,大门那边咣的就是一声大响——一辆旧面包车,一头撞在自动门上。门卫蹦着高就窜边去喊:“你瞎啦!往哪开!”面包车里没人回应,门卫急了,伸手就砸车窗。
小马跑过去,朝车里看看,突然猛地推开门卫:“快!开门开门!把大门录像关了,把这段儿抹了。”
院里这几位可不糊涂,立刻明白了八九分。叭叭跑过去,门卫说门撞坏了开不了,孙立本说都来推,推半天推出有一车多宽,车进来,小马给引到食堂房后,对车里说:“没事了,包书记,这没摄像头。”
包书记从车里出来,抱拳说:“对不起各位了,这车是我一亲戚开的,煞车不灵,那大门我负责修理。”
赵小凤说:“用不着,这门太碍事,群众出入不方便,孙镇长早想拆了。”
包书记乐了:“行啊,看来群众观念还挺强嘛,有成果!那好,就算我替你们先拆一下。”
孙立本心里说你这一下一万多块进去了。可嘴里还得说:“好,就是要和群众零距离才好。”
应该请进楼里,包书记往大院前一看,有摄像头,忙退回说:“咱在伙房里说吧,很快。”推门就要进。韩大平说:“这边,那是库房。”
进了伙房找个单间,让小马留在外面,关上门,包书记反客为主说:“都坐下听我说,我的前妻去世后,我又找了个伴儿。但由于我教育得不够,她背着我收过红包。我这才发现,痛心得很。所以,今天来,一是做自我批评,二是退给你们,就这事。从此,有人问起,就当这事从来没发生过。”他拿出一个大信封,鼓鼓的,能有四、五万。
太突然了!想到哪儿都想不到是这等事。不过,几个人也都明白,包书记有这举动,恐怕也是有难言之隐。说老实话,这些年县里大小头头哪有不收礼的。有的不光收甚至明要,不给不办事。当然,也有主观上不想收的。可问题是你手里有权,你一句话把谁提了,一句话把事办了,既便都是应该的,但风气已在,人家不表示表示觉得过意不去,就得送点什么。送东西,不缺,送卡,银行到处是录像,只有送钱是最简单。特别是男的天凉后穿西装,内里两口袋,又大又深,一边放两、三万新票,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有人曾认定,西装这口袋,当初就是为装美元英镑行贿设计的。中式的如中山装还有旗袍,都不行,紧贴身,装哪哪鼓,一看就看出来。
孙立本说:“包书记,您真是我们的……严于律己的楷模。不过,我来镇里晚,这绝对不是我送的。”
赵小凤说:“包书记,要我说您不必这样,这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快结束了,旁人都坚持住了,您干啥自己点火烧自己。”
包书记说:“不退清,我心里不安啊,还怎么要求你们。”
赵小凤说:“一样要求,要不是市纪检来,老白不是照样在这当书记。”
韩大平说:“这钱如果是白顺成送的,有记号,新钱,我帮他弄的,尾数按单双号重新排列。”
包书记大吃一惊,赶紧打开看,四万,有两摞真是像老韩说的排着。那两万不是,都是从一到十。包书记说:“是不是装差了,还有一包。”又拿出个大信封,也是四万,果然,各两万排序不一样。调整好,包书记说:“这就没错了,是老白送的,更得退回。另外,咱们统一一下口径,如果问到这笔钱,就说半个月前退的,那时白顺成还在位,就说他外出了你们代他收的,回来他就被叫去谈话了……”
“行,行……”
“我走了,去小钱那儿。”
“小钱儿那儿别去了,他上吊了。”
“上调了?调哪去了,我怎么不知道?”
“吊房梁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