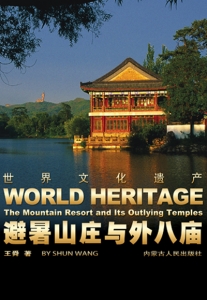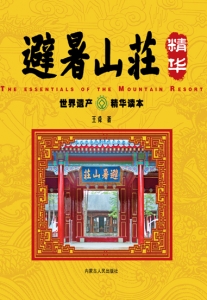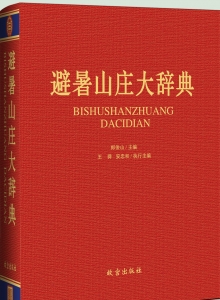二
不是给他的,是让他送礼的。
韩大平坐在沙发上喘着粗气,给赵小凤使个眼色,赵小凤心领神会,说:“孙镇长,这事可不是为你为我为他,这是为了咱们镇、咱们全镇人民。人家包书记儿子八月十六结婚,他可就一个儿子。这么大的事,咱们没点表示,你说,能说得过去吗?”
孙立本还是不吭声,接着抽烟。这会儿烟没臊味儿了,但贼呛人。孙立本怀疑这烟是假烟——县一中的校长和他是中学同学,暑假前,有位家长心也太急,转着圈儿求到他,请他帮忙让孩子上一中。事不大,他确实给说了,那孩子也上了一中。可今年的政策就是就近升初中,那孩子的小学六年级整个端进一中,想不去都不行。怪不得那天稍一客气,那家长马上就把钱收回去,分明是虚晃一枪呀……
韩大平干咳几声,意思是孙立本你别走神。
韩大平说:“小凤说得没错,这跟以往逢年过节送礼不一样。按现在的形势,甭说中秋节,就是春节,咱一分也不能送,送了人家也不敢收。可这是办喜事,办喜事呀,到啥时候,也得有人办喜事。要不然,哪来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还有啥来着?人生四大喜事?”
孙立本还是不吭声。
赵小风不见了淑女样,又回了原形,问:“你说啥,‘四大喜’?有,那个,‘活大泥,打大坯,挖墓地,操……’”
孙立本不能不吭声赶紧拦说:“打住打住!你说的是‘四大累’。‘四大喜’是他乡遇故知,和久旱逢甘露。”
韩大平说:“对对,没错没错,还是人家孙镇长肚子里有墨水。小凤,你以后得多学着点,别一张嘴就往把旁人往沟里带。”
赵小凤瞪眼:“怎么是我带?本来说的好好的,给包书记儿子结婚送礼钱,你怎么弄出个四大喜,明明是你往沟里带嘛,孙镇长,是不是?”
孙立本点头:“是、不是,是。”他心里格噔一下,完啦,没等人带,自己是主动往沟里跳的,可不跳也不行,赵小凤又要下道儿了。他娘的,来镇里别的能耐没长,说些用不着的能耐可猛见长。
韩大平拍拍脑袋:“哎哟,对不起呀,我有点喝多了。今天中午,这几个记者也太难对付了,不把他们拿下,过几天就见报了。标题我都记住了,是,‘乡村小寡妇梁红玉的饭馆兼洗浴名叫一朵红梅,让镇里给吃黄了洗垮了’。”
孙立本说:“这标题也太长了吧。”
赵小凤说:“你别听老韩的,就是想诈咱俩钱。”
孙立本问:“给了吗?”
赵小凤说:“依我,一人给他两耳光子。算啦,一人一条烟,打发了。不过,有个事你听了可别上火。”
孙立本摸摸嘴角说:“本来就有火,再来点也行。”
韩大平说:“也行?我看不行!记者说,昨天采访时,梁红玉说她肚子里有了,想吃酸的,里面那孩子可能姓白!孙镇长你搞过宣传,你说这新闻是不是太刺激人?”
孙立本小肚子发紧说:“是,是。”
赵小凤说:“她说姓白就姓白?她还说姓韩呢……”
韩大平猛地直起腰:“不可能,不可能!你别看她长得俊,有一身爱人肉儿,还总说要拜我为师,跟我学黑瞎子熊拳,可我有定力。我的原则是,在她家饭馆吃饭,可以。在她家池子泡澡,不可以。她一朵红梅,我……”
赵小凤说:“你牛粪一堆,正好给花上肥。”
韩大平说:“去!那次,她把我堵办公室里,我是跳窗户跑的。”
赵小凤说:“别吹啦,你办公室是二楼,你跳楼?楼下怎么没坑?”
韩大平说:“那、那天是堵在一楼哪个屋。孙镇长,这姓梁的娘们可不是东西了,动不动就说肚子里有孩子姓什么,对了,你坐稳了,轮到你了。今天上午她跟马主任干架,又说不姓白,改姓孙了……”
孙立本忙说:“姓孙的多啦,还有孙悟空呢!”
韩大平说:“指名点姓说的就是你。不信,咱叫马主任。”
小马随之就过来说:“是真的,她真说了。那会儿我想告诉您,您没让我往下说。”
孙立本哈哈大笑说“不可能,我跟黄小菊十来年了都没养出孩子,到这儿就能让人怀孕?除非喝了子母河的水。”
赵小凤说:“这可难说,你俩不生孩子,八成责任在你媳妇身上。现在女的要不想怀孕,太容易了。你这么好的身板,大公鸡似的,哪能不会打鸣踩蛋,你可别糟践自己。”
孙立本说:“那倒是,我也琢磨我没毛病。”
小马说:“那您可就有嫌疑了。”
孙立本说:“嫌啥疑?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怀孕的事,我也懂点,十月怀胎,我才来几天,月份不够。”
赵小风说:“十个月?那是瓜熟,这说的是怀上,做种、做胎,就是有了。”
孙立本说:“有了,也不能这么快。”
赵小风说:“初一作胎,十五不来,下个月闹小病,最短四十多天,你来大汤泉多长时间?”
孙立本看一眼挂历,算算:“差十天两个月。”
赵小凤问:“就算五十天吧。在‘一朵红梅’给你接风是哪天?”
小马说:“来的第三天。”
赵小凤掰搿手指:“完啦完啦,孙镇长,你得有思想准备呀,时间一点不差,整好对上。这事有点麻烦,从计划生育讲,黄小菊自已有一个儿子,你俩还可以再生一个,现在又放宽二眙,但让人代孕……”
孙立本蹦起来:“说什么呢!你快拉倒吧,谁让人代孕。根本没那回事!”
韩大平说:“这可是大事。如果不是代孕,就是小三、通奸,现在打老虎这都算一条。咱回忆一下,那天咱都在场,吃饭时不可能,吃完饭呢?”
小马说:“给孙镇长安排的泡汤。”
孙立本坐下摆摆手说:“都安静,让我捋捋,对对,那天吃饭,你们都说这的水好,梁红玉还说她家这股泉子是雄泉,男的泡最好……”
赵小凤说:“壮阳。”
韩大平说:“闭嘴,听着。”
孙立本说:“吃完,你们都说有事走了,就剩下我和小马,我一个人进去。泡了不过十多分钟就出来了,梁说小马刚走,去、去给车做什么保养去了。”
小马点头:“没错,孙镇长记忆力真好,是做保养,換机油。”
赵小凤问:“往下呢?梁红玉上午咋说的?”
小马说:“她说孙镇长泡完走了,她进去收拾那个池子。那池子是她家最高级的鸳鸯池,铺着防滑的磁砖,有小麻点。她说一看那池子水很干净,没舍得放,就自已下去洗……结果,就怀上了……”
孙立本问:“你说清楚,怎么就怀上了?”
小马说:“她说她坐在你坐过的地方,就是池边有小麻点的磁砖上,就怀上了。”
孙立本哈哈笑:“滑稽,可笑!我坐过的地方多了,宣传部会议室,我坐了十来年,哪个女的怀上了?”
赵小凤摇摇头:“孙镇长,我看这事你别掉以轻心。人家说的有道理。咱们都是过来的人,也不必不好意思,你说你在宣传部坐十来年女的都没怀上,关键是都穿着衣服,不信,你们都光着身子试试,那得养出多少小通讯员……”
韩大平说:“别说那用不着的,就说梁红玉怎么怀的吧。”
小马说:“她说了,那瓷砖上,有孙镇长留下的东西,她一坐,正好道路畅通,噌噌,钻进去俩……”
孙立本喊:“什么什么,还钻进去俩?她看见了?”
赵小凤说:“你知足吧,她要说你俩一个池子洗鸳鸯浴来着,你想不承认,连个证人都没有!”
孙立本冒了汗。
三
怀孕的事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只能打住。还有别的事,说得时间长点,一看日头落山了,想在镇食堂吃口饭,没找着大师傅,韩大平和赵小凤说得了你也回家吃吧。就催孙立本上车,又嘱咐小马机灵着点,注意街上的摄像头,只要孙镇长把钱给了,赶紧脱身。小马说没问题也不是头一回,车牌子都换了,让镇长坐后排,卡口摄像肯定照不着。孙立本听听头皮发麻,这怎么像是搞地下工作。他问:“你说邝春丽要回县城?”赵小凤说:“千真万确。小邝她妈是我干妈,我们是姐妹,那会儿你下车后,她就打电话问我晚上回县城不。我问她干啥晚上回去,她说给包书记送喜钱去。我这才和韩书记商量,咱们也不能落空。”
孙立本说:“那正好,你和她一块去得啦。”
韩大平说:“那哪行,她不够级别,要是副县长,就她去。这是书记,要是老白在,都轮不到你。”
孙立本说:“还有这规矩,我在县里这么多年咋不知道。”
韩大平说:“要不你咋总当副部长,还是宣传部。这回该知道咋回事了。”
孙立本说:“你们看啊,人家包书记姓包,包公的后代,咱给他送礼,那不是往狗头铡里钻。”
赵小凤说:“这你蒙不了我,我爱看戏,包家还有包勉呢。”
孙立本说:“长亭铡了。”
赵小凤说:“那他也有后人,古时候人结婚早,韩书记,你的前辈是韩信吧,多能耐,那后辈儿也有韩、寒流……”
韩大平说:“还感冒呢!跑题儿啦跑题儿啦。”
赵小凤的手机响了,是邝春丽,说她已经从小汤泉出来了,让赵小凤做好准备,另外,说魏老板已经在县里等着,今天晚上可能战个通宵,让她把那副麻将带上。小马耳尖,听了就从后备箱拿出一个方盒子,递给赵小凤。赵小风接过来说快走吧要不就碰上了。孙立本只好上车,小马开起来一阵风就窜下去。在车上,孙立本问是哪个魏老板,小马说是小汤泉娱乐城的老板,挺有钱,跟邝春丽赵小凤关系特好,但这个魏老板属瓷公鸡的特扣门儿,邝春丽和赵小凤就从网上买了副透视麻将,隔三差五宰这魏老板一下。孙立本问魏老板叫什么,小马说不知道,听说他早先在剧团翻跟斗……
车子猛地一颠,孙立本身子咣的就仰到后面。小马煞住车,探头瞅瞅骂这谁干的,挖了沟也没个警示灯。又回头问您没事吧。孙立本心说白天颠我一回了,说没事开车吧,心里却像热水开了锅。他太知道这魏老板是谁啦,他就是黄小菊的前夫,叫魏宝良。魏宝良当初在评剧团演过小生,也会翻跟斗,人长得太帅,不少女的被他弄五迷三道的。他也特自傲,本团那些女的都看不上眼,最终看上了县里才成立的小歌舞团台柱子黄小菊。黄小菊论模样没的挑,论心眼就不行了,傻不叽叽的叫魏宝良一通花言巧语就给弄到手,结果呢,魏宝良花花肠子,结婚后没多久又跟别的女人好上了,就闹离婚,为这黄小菊差点没上吊。后来魏宝良就走了没了音信,这么多年,不露面也不给孩子抚养费,黄小菊说就当他死了。孙立本嘴不说心里说但愿真死了,谁会想到哪块墓地偷工减料这会子他又钻出来。
快进县城时,身后有车灯闪,小马惊叫:“宝马535,漂亮!邝书记的车。”孙立本问:“不是我早上坐的那辆?”小马说:“早上敢开这车?这是她新买的,五十多万,您服不?”孙立本说:“服,她可真有钱呀!看她那样,挺本份的一个人。”小马说:“对,‘本份’,又有‘本’又有‘份’。”孙立本说:“什么意思?”小马说:“这您还不知道,用我说?”孙立本说:“我是真不知道。”小马说:“那咱哪说哪了,我也是听人说的,人家邝书记最早是县电视台的播音员,后来上面派来个古副县长,他们就认识了,再后来邝书记就进了政府办,再后来古副县长当县长,邝就当了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古县长回市里当交通局长,邝就下乡当乡长,再后又来小汤泉当书记。”孙立本说:“多磨叽,什么再后来再后来,你是组织部管人事的呀。我是问你‘本’和‘份’?”小马说:“这还用问吗,人家有身子,那是本钱,人家圈子里又有股份,那是份钱。”孙立本问:“股份?什么股份?”小马说:“养廉股呗,您也该有吧?”孙立本一愣:“什么养廉股?我都没听说过。”小马猛地跺住煞车喊:“我操的,这车是怎么开的?这么小窄路他敢逆行!”
小马挺猛的,推开车门下去就要干架,孙立本赶紧也下来,心说这可不行,一吵吵那不暴露了。到车头一看,对面一个崭新的四圈奥迪,车上下来一位,天都黑下来还戴着墨镜侦探似的,小马突然喊哎哟哟冤家路窄这不是老同学嘛,你啥时换的车;孙立本仔细一看也乐了,原来是今天和自已坐一个车的小钱书记。大、小汤泉这趟川有四个乡镇,小钱在中水泉,离县城近。近也有四十里,这小子挺能忽悠,那会儿他在车上还说晚上要开会,这会怎么开到这来了?小钱也认出孙立本,俩人倒挺绅士,点点头就站到路边树后,小钱说:“你也来了?”
“来了。”
“去开封府?”
“嗯,对。开、开封府。”
“搬家了。”
“那咋办?”
“问问王朝马汉。”
看来小钱门清,给包书记秘书打电话,秘书说包书记说了,谁要给他送礼,就有劳送到上午去的那个院里五一四房间,那有人收。
“五一四房间?”孙立本不解。
“五一四,‘我要死’。”小钱说。
“那就不送了?”孙立本问。
“不行,这不还没死嘛。唉,活得真累呀………”小钱叹口气,又说了一件事:前些天有位县领导,孩子结婚,本来大伙都不知道,是他秘书打电话,说千万不要送礼。考虑到这阵子从中央到省里市里一再抓这些事,这是领导在给大伙打预防针呀,挺好的,小钱就没送。结果呢,一打听,完啦,婚礼上是见不到礼金台,也按规定没超过十五桌,可私下里,照收不误不说,比当众记帐给的还多。完事再见到这位领导的面,小钱就觉出有点异样了,人家的意思是提拔你时我说过话,你还跟我玩这套,可把小钱给悔死了。这回倒真的不是包书记秘书提前打电话,从哪传来的他都不知道,但这根神经太敏感了,官场如战场,一步棋走错,再想挽回来就难了。
小钱说拜佛不见佛面,咋也见佛腚,啥都见不着就白拜了。孙立本说归其在乡镇头把交椅上是新兵,何况还是临时主持工作,别看小钱比他小,已但当书记好几年了,关键时刻就得听人家的。他就叫小马开车开跟着小钱走。关上车门,小马说小钱最近精神有问题了,可能有点抑郁。还说小钱从小心眼多也心眼小,在师范念书就会给老师送他爹种的大叶烟,功课不行也当班长;他爹老了常摸着柏木棺板,见人就说我儿子孝顺呀,其实那板子是小钱朝一个老板借的,他爹死后装的是柳木棺材,价钱差不少。可他自己新广本没开几天又换奥迪,你说他得有多少钱。孙立本听着心里怪不是滋味儿,由不得说:“啥木头到地里也烂成泥,啥新车……”。”
小马精明,知道可能哪里刺着了孙立本,忙说:“嘿,结果呢?下葬时,小钱可能觉得对不起他爹,一磕头,劲使大了,头晕,一起来,一头扎到坟头上,鼻梁子骨折,大家都说他今年可能有大灾。”
“是吗?听说有那么件事,原来是他呀,哈哈。”孙立本笑了,突然觉得笑得不对劲,这是什么心理?赶紧停住,没话找话:“这是去哪儿?别真去了‘五一四’房间?”
小马说:“找着了,瞧,前面不少车呢。”
在一个新建小区大门外,路灯明晃晃,小车一大溜,小钱下车过来对孙立本苦笑:“没错,大部队在这儿呢。”孙立本一看,我的娘,上午参观的那些人差不多都到齐了,心照不宣,仨仨俩俩的戳着也不说话。过一阵,有两位从院里出来,说:“诸位,大家的心意,包书记都领了,但礼是绝对不能收。都请回吧。”“那都谁来了,书记知道不?”“知道。”“知道就好。”
得,佛腚?还佛屁都没闻着,那也得走了,多数人回家,没几个回乡镇。现在乡镇干部家都在县城,小马家也在,他说他今天晚上有要紧事,得明天早上回去。孙立本不会开车,问有什么要紧事,小马说他已经批下二胎指标,这些日子没喝酒也没抽烟,就等着他媳妇的“日子”,今天就是。说话间车停了,孙立本一看这地方好熟悉,是自已家。他说:“不对呀,我也不要二胎,我回家干啥?”
小马说:“住一宿吧,嫂夫人年轻,长的又那么漂亮……”
孙立本说:“漂亮有啥用。”
小马说:“您可别守着美人不当回事。我一亲戚的孩子六岁一百斤,小肥猪,非让去文化馆学跳舞,后来那亲戚说实话,就为接送孩子看一眼黄老师。”
孙立本说:“瞎编,瞎编。不行,镇里还有事呢,明天还要开会。”,
小马说:“这会儿回去,梁红玉准等着呢。”
孙立本一听梁红玉仨字,立马下了车说:“梁红玉、梁红玉,她不是韩世忠的媳妇吗?这个娘们,不好好在金山擂鼓助战,到本朝来捣什么乱呀!”
小马说:“知足吧,要是白骨精,更麻烦了。”
孙立本说:“别关手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