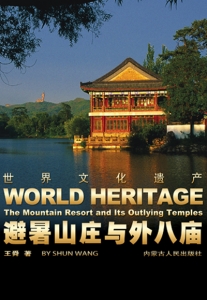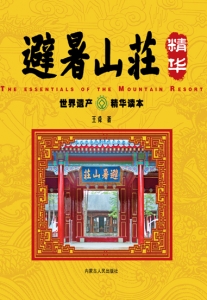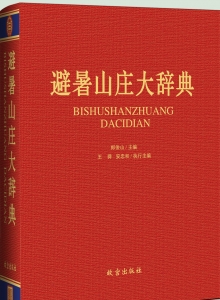我在1978年前后
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旁有一条沙土路,前方不远处的山叫松树梁。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松树梁沟里的坡地上收棒子。准确地讲,我是扛棒子的,一麻袋、一麻袋地从地里扛到路边,再装车拉回位于大佛寺前的承德地区“五七”干校。那天,我扛得很欢实,来回一溜儿小跑。
午饭在食堂,我要了个肉菜,并破天荒地造下八两大米饭。有人提醒我:“超标了。”我大口吞咽着,呜呜地说:“这回好了,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这是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台词。
我是1976年暑期从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因当初是从承德地区上学的,而承德是贫困地区,要求送出去的学生必须回来,所以读书三年在保定,眼瞅着距天津近了一步,却一竿子又被打回塞北,再分配到地区“五七”干校当教员。当教员也得干活,干活我不怕,但我怕口粮不够吃:我每月定量29斤,单身汉,吃食堂,没油水,越吃肚子越没底。因此,我必须严格按照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的标准去吃,才能确保后半月每天能按时进食堂。
但那天我放开了肚子美美地吃了一顿,原因是我有了一种预感,期盼已久的“春天”,可能就要到来了吗?但必须说明,那只是一种在内心期盼又不敢盼的期盼:“文革”十年,“斗批改”口号喊得震天响,最终变成多少人回家“逗孩子、劈柴火、改善生活”。预想与结果完全脱节,稍有头脑的人都会觉出这十年折腾有些问题,即便如此,有朝一日能把“文革”翻个个,在当时还是不敢想。
普宁寺内的大乘之阁,有一尊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佛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因此又称大佛寺。大乘之阁门额上的蓝地金字匾,为清乾隆皇帝所书,四个大字是“鸿庥普荫”。意为佛法如宏大的树阴,庇护普天之下的芸芸众生。我曾多次站在“鸿庥普荫”下,心中暗暗祈祷,但愿国泰民安的日子早早到来。
这年我已经26岁了,当务之急,是搞对象成家。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并非难事:身高1.78米,体重124斤,宽膀细腰,要文能写文章上讲台毛笔字能写楷隶行草,要武会洗衣服做饭套炉子搭灶台,论模样,同事母亲看了黑白电视新闻联播,说那小何老师跟赵忠祥一个样……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二十多岁的小伙风华正茂,还是有点儿骄傲本钱的。
不过,这点儿本钱很快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了南墙,输得精光──大约整整一个1977年,从春到秋,马不停蹄,披星戴月,谈了不下十来个对象,几乎都因为我的家庭情况和本人不是党员而败下情阵,铩羽而归。
版本大都相同:经人介绍见面,看得上眼、谈得来就往下再谈,双方有了感觉后,或者是女方本人,或者是家长介入,问你是什么出身,你父亲在“文革”中是怎么死的,你怎么不是党员?
不用多了,就这三个问题,人家就高悬免谈牌说拜拜了。其实我家事情并不复杂,也能解释清楚,但那时哪个女孩、谁家父母,不想找一个根红苗正的?对此,我也是完全理解的,一点儿也不怪人家。
眼睁睁看着身边比我岁数还小的男同事都有了女朋友,唯独我只听锣响不见人来,心中好生着急,但也只能安慰自己──好事多磨,失败了还可以再重谈,相信总有谈成的那一天。
闲言少叙,隐私不言,功夫不负苦心人。初冬,我终于遇见了一位不在乎上述三点,并自己能做主的女士,而我也不问她家的情况。我们只谈现实,不谈历史,只谈前景,不谈身份,于是就成了一家人,她,就是与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儿。然而,话说得容易,其中的沟沟坎坎则多了去了……
当时在机关单位,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男女青年交朋友,要结婚,不光党员,就是一般干事,也得向领导(组织)汇报。领导同意,才可以往下进行,不同意就得散。其中的红线,就是对方家庭出身(成分),以及父母有无历史和现实问题,等等。
关键的1978年到了。
年初,我决定要在春节前结婚。开介绍信,领导一愣:“你要结婚?怎么不提前汇报!女方家什么情况?”
我还是有咱天津人个性的,说:“咱们是‘五七’干校,除了种地就是养猪,有那个必要吗?”
领导不爱听,说:“种地、养猪怎么啦?这是规定,必须遵守。”
我知道只要一走程序,肯定不行,心一横说:“我又不是党员,也没人告诉我啊。”
领导说:“那你以后还当教员不?”
我说:“如果不适合,可以不当。”
这些话放在先前,打死我也不敢说。此时,不可阻挡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潮流,让我胆子大了些。当然我也清楚,即便不当教员,也丟不了饭碗,最不济就是种地,我也不是没种过。关键是不能去审查,我老伴儿家有点儿房产。
但事情也怪了,没过两天,就有人把信开给了我。登记、结婚,从此我有了一个家。后来听说,我结婚的事汇报到校领导那里,班子正开会,有人说挺大岁数好不容易搞个对象,成全了吧;有人说他不是党员,干校可能要恢复为党校,到时他也没资格当教员了;还有人说过了年就调他去生产科,也省得他在课堂上跑题乱讲。
春节过后,关于是不是将我调出教研室,上面有了分歧。两年前一同分配来的十个学生,几乎都进教研室走了一遭,有的半年,有的俩月,或者一试不适合当教员,或者自己要求走,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一致公认的是,此人是个难得的教员材料。有实例为证,包括外出学习、临时借出去帮忙,甚至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别人不愿意去,我主动要求去都不让去,一直拿我当教学骨干使。所以有人主张再观察一段,不急着调出。往下,形势变化很快,有的领导就觉出我的一些所谓“乱讲”,有的恰恰是对长期以来某些“左”的理论和做法的不满,于是就改变了看法:这个人不仅不能调出去,还要重点培养。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难点:我不是党员,看不了红头文件。
要说我是十分要求进步的:在乡下加入了共青团,还是团干部。参加工作后,无论是想着为解放全人类奋斗终生,还是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当教员本身需要是党员,还是搞对象时因不是党员受过刺激,总之,我入党心情之迫切,绝对非一般上进青年可比。
然而我又有难言之隐,我父亲从小学徒当的是店员,解放前一直经商,“文革”中就为这把他折腾得患病去世。不搞外调尚好,一外调反而添麻烦。可事到如今,也顾不上许多了,我得继续要求进步。
外调的回来了,结果超出我的预料,我不但没进步,反倒连入党积极分子的人选也不是了。我很苦恼,找到党小组长,说不是重在个人表现吗?他倒也实话实说:话是那么讲,但自“文革”以来都这么着,认倒霉吧。
赶上这不讲理的事,不认也得认!入夏,又有新班开课,讲唯物论、辩证法,我想了又想,事物都是发展的,凭什么就把这套理论和做法当成宝典捧着不变?加之家里日子不好过,情急之下我去找校长,说:“我看不了红头文件,这教员我不当了。调我去总务处,最好是去当伙房管理员,起码能往饱了吃……”
校长当时就拉抽屉拿出十斤粮票:“你不够吃说话,多好的小伙,放心吧,组织问题,我们已有新的考虑,会抓紧解决的。咱们是党委,有发展党员的权力。”
话说到这份上,我不能再说别的,粮票不要,继续认真教课。到了八月份,万万没想到,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很激动,平静下来想:我还是先前的我,怎么说不行就不行,说行就行了呢……
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让新党员发言,我诚心诚意地说:“我觉得我与党员标准还有很大差距,这次能被通过,主要是因为工作需要……”
往下我还有话呢,但不能说下去了,所有的人大眼小眼一齐瞪我。小组长立刻让别人发言,把气氛缓和下来。会后,他急赤白脸地跟我说:“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说:“那我该怎么说?”他说:“你只要说些感谢组织、感谢领导、感谢同志的套话就行了。”我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他说:“这么多年了,就没见一个像你这样的,有些场合是不能讲实话的!”
不管怎么说,我终于走进组织的怀抱中。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交党费,就在我所在的教研室大屋,很多人在交,我没交过,又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过去人家交党费时,我得知趣地避开,现在终于不用了;紧张的是,不知道交多少钱。轮到我,组织委员说:“你交一毛钱。”
我从工资袋里往出掏,嘴里磨叨,噢,一毛钱。偏偏此时有谁问:“你第一次交党费,不说点什么?”一下子把我弄紧张了,本来挺利索的嘴,突然变成棉裤腰,说:“一、一毛钱,比团费贵啊……”
完啦,屋里顿时鸦雀无声,大家都瞅我。我说:“我可不是嫌贵,团费是交五分……”
党小组长立刻单独找我谈话,问为什么心疼那五分钱,让我挖思想根源。我说我真不是心疼那五分钱,是说走嘴了,要不我把这一个月工资都交了,表表忠心。我真的去交,没找着人。中午回家,爱人怀孕了,说你发工资了,咱炖点儿肉吃吧。我说正要跟你商量,我想把这个月的工资都交了,媳妇说,最好把你自己也交了。
谢天谢地,此事没人深究。我知道自己还在预备期,一年后才转正,必须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行。一段相安无事,秋去冬来,十二月中下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大事,更是我们理论教员关心的头等要事。那时的大教研室,一个大屋十几个人,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又多聊时事,各抒己见。有的人赞成,有的人则认为还得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才能目张,等等。看人家说得欢,却不对我的心思,我忍不住说:“纲举了这么多年,只见百分之五的队伍在壮大,三十来斤粮食定量可没见增加。”立刻遭到反驳:“是抓阶级敌人重要,还是抓粮食重要?”我说:“月月都见你去粮店买粮,啥时见过被专政的人到你家搞破坏?”
这就不仅是话不投机了,往下,也就无法在一起聊什么了。我也知趣,索性晚上呆在家里。况且,女儿出生了,我要伺候月子。北风呼啸,屋里的墙上布满冰霜。清晨起来,外屋的水缸结了一层冰。正月里,女儿满月,爱人带孩子住到娘家,我看家中连把椅子都没有,就找点旧木头学着打了一对简易沙发。住在家属院,我也没背人,还傻乎乎叫人来看看我的手艺。不料,开党小组生活会,有人就提出批评,说你晚上不来备课,却在家搞安乐窝。紧接着就有人捯老账,说你结婚回来竟然穿一件新呢子上衣,这是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还有好几件事,如哪天哪天你私下跟谁说过,总这么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不是搞得太紧张了,你还曾抄录鲁迅“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诗句,贴在单身宿舍墙上,等等,这都是什么意思?我的天呀!这都是哪年哪月的事了?人家都给我记着账呢!
我据理力争,敢说不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壮了胆,倒使总盯着我的人也没了办法。春暖花开,大佛寺游人渐多,个人开始做生意,我家后窗下就有拉骆驼照相的,小饭馆也如雨后春笋般接二连三冒出来,农贸市场可以买到鱼呀肉呀,人们脸上也多了笑容。面对生活的变化,我欢欣鼓舞,回天津探亲时在百货大楼,花一个月工资买了个半导体。星期天在小院里烧灶做饭,逗女儿笑,听于淑珍唱的“清清的花溪水,绕村向东流……”旁人见了,说生个姑娘就这么高兴,要是生个小子,还不得美出鼻涕泡儿来!我说明年我就冒鼻涕泡儿!
女儿三个月时,学校开大会讲现在提倡只生一个。我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又生了女孩,还想再要一个,就没报名。过些时,全校开表扬会,奖励报名的每人一个大床单、一把暖水壶,只我一个人没有。领导找我谈话,问你怎么不报名?我说不是只提倡没说必须吗?领导说你怎么还犟死理呢,提倡就是必须,否则,你就别想按时转正。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没了办法,只好去报名,然后去领床单、暖壶,人家却说已经没有了。
几件事汇合起来,我感觉不妙,到了一年头上,果然没人提转正一事。我也不敢去问,干等着吧。直到冬天,有个晚上我正在家写小说,党小组长找来告诉说你转正了。没等我说啥,他说今天咱不说套话,先去我家帮我一下,沙发扶手的卯榫,我不知怎么交代。我一听急了,说先前批我搞安乐窝,如今你们怎么也搞起来了。他笑道,这不是思想解放了吗!我还能说什么,只能笑了说好。
一轮明月下,家属院内一片欢声笑语──拆土炕换软床的,安装土暖气的,打沙发立柜的,买了黑白电视看《加里森敢死队》的,连房后庙寺飞檐悬铃都叮当欢响,分明是告诉人们:人们心里的春天,已经乘着浩荡东风真的来了!
自打与人争论后,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小说了。因编辑部退稿退到收发室被发现,就引来教研室一位负责人的批评,认为我是不务正业,并讥笑说小说可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出来的。而我当时也确实屡投不中很是苦恼。一天,我的插队老同学从县里来地区开会,我们见了面。他在县城小学当老师,与村里联系密切,他说了村里发生的很多新鲜事,我很受启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不能闭门造车,应该走出校园,深入到火热的农村改革开放大潮中去。
转眼到了1982年,在一位新来校长的帮助下,我调到地委宣传部,原有的两间平房一个小院全不要了,住进爱人单位十平方米的筒子楼。我不爱坐机关,经常下乡,看到听到许多发生在乡村的新鲜事,接触了很多有特色的致富带头人。很快,我的小说就受到报纸杂志的喜爱,屡屡被刋登。到了1984年,年初我从干事提拔为宣传科长,年末又提升为地区文化局局长,成为全地区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同时,我的中篇小说已在国内大型文学刊物上发表,而在党校那里,我又成了他们的新话题──那个何申,原名何兴身,他能有今天的成绩,都是我们培养教育的结果……
多年后的一天,瑞雪飘飘,我陪客人去大佛寺,在大乘之阁前,遇见一位干校、党校的老同事,当年他是一听说要搞运动就兴奋得眼珠子放光的人,现在则变得稳当多了。他见我抬头看“鸿庥普荫”那块匾,说:“大佛有灵,可以让众多人同享福荫。”
转身凭栏眺望,眼前是我曾经住过的家属院,不远处是避暑山庄的宫墙和热河老城区,再往远望,山峦起伏银光闪烁,塞外大地充满着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