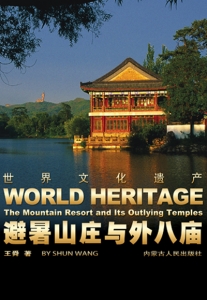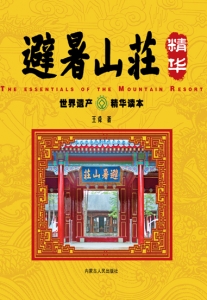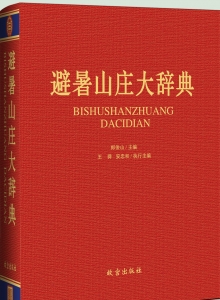他是真的犯难了,难处有两点:一是此时是否离开热河,去北平或天津躲一躲,那边早备好了房子。但自己在这里是有身份的人,热河商会会长属头面人物,你一动,商界皆动,市场溃散,物价大涨,到时候说你不负责任都是轻的,说你动摇民心破坏抗日大局,你都没法反驳。二是热河正月花会极有传统,规模宏大,誉满塞北。而二爷就是当下的花会“会首”,换句话说,就是花会的总舵把子,办与不办,办好办赖,都在“会首”一人身上。若是这些时中国军队把日本鬼子打跑甚至挡在城外,到时花会一闹,这“会”就是慰劳英勇杀敌的将士;可万一没挡住,小鬼子杀进来了,偏你这厢又弄着民间的热闹,那就麻烦了,兴许就说成是欢迎皇军,如此岂不成了汉奸,弄不好还要掉脑袋……
我二爷年轻时,是第一批留日的公费生,在日本呆了好几年,深知日本人的小心眼子。就说在福冈吧,有一位与二爷交往算是很不错的当地朋友,叫藤山一郎,对中国文化挺感兴趣,但又从心里认为他们大和民族的东西高人一头。比如他跟我二爷说,他家乡有一民俗:人骑着大木头从山上往下滑。这个我曾在电视上看过,应该说场面很刺激:两三个人搂不过来的大树去了枝杈剥光树皮,四五十人骑马似的骑上,从约有45度的山坡上往下出溜儿,又在冬季雪地,弄不好说把人压扁就压扁。
按说国情民情不同习俗不同,各有所长,无所谓谁高谁低,但藤山一郎太傲气,硬说中国民间迎春活动,没一个能顶得上他们骑木头的一半,多牛气,还一半。我二爷当年也是血气方刚,嘴茬子不饶人,上下嘴唇一碰,说在我们热河,小孩子卵子痒了才骑木头蹭,你要是不怕疼,就把你那篾席割的单眼皮小眼睛睁大瞪圆,到热河去看看我们的正月花会!藤山一郎就真跟尖刀扎了卵子,嗷嗷地叫道:“我一定去看!”
我二爷当时点头说:“好,一言为定。不让你心服口服,你就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藤山一郎问:“谁是三只眼?”二爷说:“二郎神!”然后,他还专门为当地的朋友搞了一次讲座,题目就是《中国春节民俗与北方花会》。二爷他怎么有这方面的知识呢?除了看书,更主要的是他父亲也是我太爷曾是热河大名鼎鼎的花会“会首”。说来挺有意思,别人家盖房套大院,空地上都弄些假山假水花廊曲径。当年何家大院则不同,一水的黄土平地,跑得了马舞得了龙,一边还有几排横杆和矮墙,为初学高跷者当扶手和“板凳”。一年四季,这院里操练不断,到了腊月正月,就愈发人声鼎沸。我二爷在这环境里长大,不光耳濡目染,还亲自下场,舞得龙灯踩得高跷扭得秧歌练得武会。热河花会36大档72小拨,他如数家珍,故此,他一讲,多数日本同学都点头称是,连藤山一郎也安静了几分。
况且,那藤山一郎下海游泳被大浪卷进深处,还是我二爷把他救了出来。藤山一郎曾结结巴巴用中文说:“滴水之恩,我当涌泉相报。”别人指着地上的一大摊水:“你,吐出有一桶,怎么是滴水之恩?”藤山一郎尴尬地说:“对,是大海一样的恩。”我二爷说:“只是希望我们只存在友谊,不要无事生非。”
这话在当时属心照不宣,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九·一八”,他们把东三省占了,蒋介石又请国联视察又以夷治夷,以为能有效果,谁承想,日本人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得寸进尺,矛头直指热河,要把热河变成“满洲国南部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