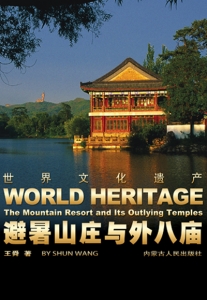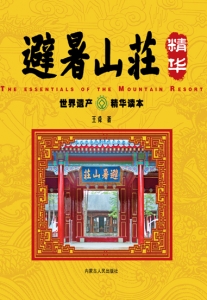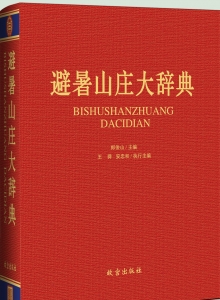约好了似地,把他看在那里。那男孩站在树下的荫影里,这么多眼睛观着,脸上便现出了手足无措的样子。因是自家,自家的院子,女孩便一一介绍这是张娘,那是李娘王娘(我们这里不叫姨,只叫娘)。几个娘的眼里便闪出晶莹的喜悦:人挺般配,郎才女貌!说话间,又见女孩摘去男孩肩上一根头发,很大胆的,便知女孩对男孩的喜欢,胜过了男孩对女孩。
出嫁的日子说来就来了。她是这个院子里,第一个嫁出去的女孩,自然要弄出个十分隆重的仪式。提前几天,娘家人就不再许她离开了,院子大门里,存放的是一个已经长大的女孩。像是一只即待飞出的鸟儿,女孩每天呆在家里,脸上呈现着无限的喜悦与期待,有时的眼圈,却是红的。一个女孩子,从下生便长在这样一处院落,吃过张娘的奶,喝过李娘的粥,真待离开,自然会有心中的一番波澜。接走那天,人哭得特猛凶,扑上去先搂住了自己的妈,再搂爹再搂弟,怎么一个出嫁的场面,如同上了杀场似的呢。
女孩子,是被一拉溜儿黑色轿车接走的,头一辆车身铺满了鲜花,从这胡同开出去的,便是一条铺满鲜花的路。送走了女孩儿,几个老女人还要在院子里抹一场眼泪,一个说:
要是我闺女,就不用黑车,我用红色的。
一个说:黑车才是高级的,你那老眼就没瞧见?中央首长坐的都是黑车。你没见那辆头车吗?顶满鲜花的。
日子过得这么快。一年之后,她便抱着孩子住娘家啦。女人的身上,多了一些奶香,人也变得有些粗糙,遮蔽了的,是作姑娘时那种单纯的情致。她有时,也会对身边的女人抹一些眼泪,那边,大概,估摸着发生了一些事情。哪家又没些事情呢,比起当年身后宫墙里,这才叫人间烟火。院子里添了人气,那孩子“呜哇”一声哭了,一泡尿把人湿了身,真是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已经被这孩子长了个凭大的辈份了。
也是从什么时候,我们这大片民居便消失了。因为城市建设的需要,因为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墙附近不可再有房屋,大杂院里的人,全部搬进了远处楼房新居。这里,己经变成了一座大型游乐场,代之以青砖灰瓦的是过山车、蹦蹦床以及大片的绿地。
有时,也会领着孩子过来玩,看着那些飞飞转转现代化的游艺,就觉恍如飞逝的时光。新鲜的草地上,依然会辨出哪一块是当年的院落,哪一块曾是我居住的房屋,甚至连我床铺的位置也能认得出。还有,那间厕所,那扇院门,夜色下发出的响声,院子里的欢闹,惟有那棵老槐树,挺立在风中倍显沧桑。时光的牙齿,又是何时把那些光阴啃蚀掉的呢?
散了伙的大杂院,散了火的人。新居里已经有些老人难以下楼了。牵挂,并不可舍下,依然伏在悬起的阳台上,隔窗相望说些家常话,那脖子探在窗外的样子,像是悬在半空中的两颗梨。又如,两棵树上的两只鸟儿。
不同的是,住在各自门号里,我们最近的邻居,比如楼下楼上或对门,却极少往来。促狭的楼道见了面,淡然笑一下,或正常的无任何表情,各自的家门,是极少被人推开的。
每年春节,我们当年院子里的老户,还是要坐下来的,为着一次聚餐。聚餐,也是有规有矩地轮转:今年这一家,明年那一家。就在这样的轮换中,餐桌上的人也在一年年减少。其实,这世上,从开始就没有不散的宴席,宴席是留不住人的,就连这漫长的岁月也留不住。看着眼前的人,又如看着自己的陈年老照片,一年又一年,不可改变地,证明着我们的衰老与年轻。
其实,这也是从一棵始终生长着的树开始的。那棵树,上百年了吧,依然枝繁叶茂地立在那里,在风中,在日光照耀下,在一场倾盆大雨之后,在那道彩虹的臂弯里,在塞外之雪的怀抱,看上去很像我们那个微缩的胡同。有些事情,人,真是抵不过一棵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