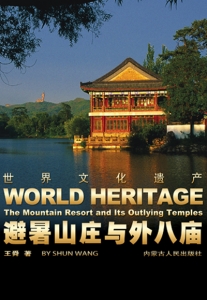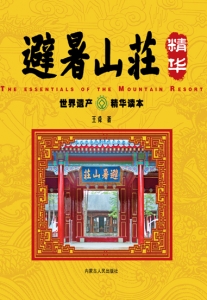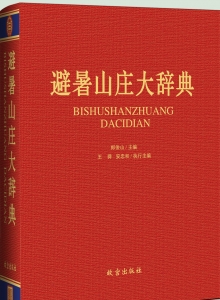大鞭在握 威震山河
宇宙,苍穹。
银河浩瀚,日月星辰如同无数的珍珠散落在漆黑如墨的大玉盘里。
蔚蓝色的地球上,湛蓝的天空,白云朵朵。万里长城宛如一条巨龙在祖国大地上盘旋飞腾,雄伟的金山岭长城屹立在家乡。燕山山脉逶迤挺拔,滦河玉带般在群山碧峰间灵动跳跃,这群山大河俨然是有了生命一般。
旭日东升,老公山云雾缭绕,滦河清澈的河水泛着金光,两边广阔无垠的稻田,碧绿的水稻正绣穗儿,淡淡的稻花儿清香如在鼻端。宽阔的柏油公路上,三套儿枣红马拉着的水曲柳大车稳稳行进,大车上苦梨柴禾码得像一座小山,一个长胡子老人手端大鞭,两脚叉开站在车踏板上,“小子,爷爷教教你啥叫上坡儿呼梢子。”大鞭抡开,一尺多长的大红鞭彩儿一团火般跃动在湛蓝的天空里,水曲柳的大鞭座子划出几圈儿耀眼的光茫,啪啪、啪— “驾!!!”
“爷爷,给我—”
大鞭递过来,我却一下醒了,原来却是南柯一梦。
眼前是满玻璃的装修,双层玻璃干净明亮。外面天色不是太好,最后一抹淡红的斜阳恋恋不舍的留在粉色的窗帘上,和鲜红的大窗花儿让屋里充满了温馨。雪白的天花板,大吊灯,新家具,新年画儿。我定了定神,想起来昨儿个慕名来拜访还留着一挂大车的三姑父,一家人盛情款待,想是澹泊敬诚的青花瓷大黄米酒喝多了,三姑父就把我留这儿住下了。看看旁边,炕桌儿还在火炕中间放着,美酒佳肴都拾掇下去了,放着一把茶壶,俩茶杯。白瓷茶壶上一对儿蝴蝶儿,壶盖儿上两个蓝字儿:前进,显示出这是有年头儿的老物件儿了。
“侄子,醒啦?你酒量儿还得练哪!”
“是是是,三姑父海量。”
“起来,喝口茶水儿,咱们爷俩好好儿唠会儿。”三姑父给我倒了杯热茶。我赶紧道谢,掀开年前新絮的大被坐起来,“三姑父,你再好好儿给我说说怎么赶大车,你瞅过那老电影儿《青松岭》么?”
“瞅过。”
“那上头万山大叔跟秀眉说的那几句‘起车要稳,进门儿要慢’我明白,‘拐弯儿靠辕子,上坡儿呼梢子’是怎么回事儿呀?”
三姑父本来一直乐呵呵儿的,这会儿却表情凝重起来,“啊,这个呀,梢子就是梢马,上坡儿全凭梢马使劲呢,你可不就得吆喝着点儿么。上坡打梢马,下坡儿拽辕马,上坡儿你瞅哪个梢子马套耷拉了,哪个马就偷懒儿呢,你就给它一鞭子。”
“梢马就是拉长套的马吧?”
“嗯。那前儿咱们大队两挂大车,都是三套儿。我们家你爷爷是咱们队大把,赶那挂好使的,俩梢子跟驾辕的都是骡子。那匹驾辕骡子最好使,能坐住车(下坡时辕马屁股往后坐,防止大车溜坡)。老孙家我大叔,你得管叫大爷爷呢,他赶那挂孬点儿的,梢子跟驾辕的都是骟马。”
“啥叫骟马呀?”
“就是阉了的马,没有七情六欲,干活儿也没劲儿,驾辕坐不住车。”
“哦。你说的下坡儿拽辕马,就是电影儿上说的‘下坡儿拽紧急缰绳早使闸’吧?”
“嗯,下坡儿前儿可不得把辕马拽住了呗。”
“三姑父,生产队前儿大车都干啥活儿呀?”
“那可多了,春起拉粪拉化肥,收秋儿送公粮拉粮食,拉棒秸稻草豆葛脑儿。谁家修房盖屋,都得大车从石条沟往回拉石条,冬天从老仟儿梁往回拉大柴火。”
“那种地趟地挑地呢?”
“种地趟地都是老孙家你大爷爷的活儿,挑地有拖拉机,你爷爷就管赶大车。那几年你爷爷跟河北柳台敞沟门儿那仨大车把式一块儿上滦河钢厂‘搞副业’,那会儿哪来那么些汽车呀,全是大车拉,他们老哥儿几个也是一天八个点儿,下了班儿左近谁家修房盖屋,都找他们给拉砖拉沙子,那几年挣点儿好钱。你爷爷疼孩子,一年回不来几回,哪回回来都给孙子孙女儿带好吃的。”
“三姑父,爷爷赶大车的大鞭杆子有多长呀?”
“赶大车得有两把鞭子,二鞭跟你个儿差不多,大鞭得有从炕沿到后墙这么长,大鞭座子这么壮。”三姑父把俩手拇指食指一圈,比划了鸡蛋粗细。
“那得挺沉的吧?”
“那敢情,你俩手够端了。”
“那鞭梢儿呢?”
“鞭梢儿可有讲究,大鞭响不响,全靠鞭梢儿好不好,你爷爷用的都是最好的黑狗皮鞭梢儿,大鞭甩起来那叫一赫亮,也有劲,一鞭能削断两颗棒秧,齐刷刷儿的斜碴儿。房檐儿上落个家雀儿,你爷爷一大鞭下去,家雀儿脑袋掉下来,身子还在瓦片儿上站着呢。”
炕桌儿这边儿,我听得出了神,端着茶杯忘了放下。三姑父拿起枣木杆儿的火烟袋锅儿,“小子,给我装上,我抽一锅儿,给你讲讲我跟你爷爷从石条沟拉石条的事儿。”
“哎!”我赶紧过来给三姑父装好一锅儿烟叶,打火机点着。三姑父嘬了几口儿,看着挺好抽。我忽然起了好奇心,“三姑父,给我抽两口儿。”
三姑父递过烟袋,“尝尝吧。”
我把翡翠烟嘴儿含进嘴里一嘬,浓烈的辣味儿立刻钻进嗓子眼儿,赶紧拿下来一阵咳嗽。三姑父乐了,“你慢点儿,好好儿尝尝,三姑父这烟味儿可正。”
我又慢慢儿嘬了一小口儿,三姑父笑呵呵儿的问:“怎么样?味儿正不?那烟叶儿我搁羊圈吊过。这可是你爷爷留下来的独门儿秘方儿,咱们爷俩投缘,三姑父才跟你说。”
我又嘬了几小口儿,三姑父问:“好抽不?”我说:“好抽是好抽,就是太重,我抽不了。三姑父,给你。”
三姑父接过烟袋锅儿,一边抽一边道:“那些年谁家盖房子都从石条沟往回拉石条,拖拉机上不去,就大车上去了。装完车下坡儿,大车后尾把子还得拴上一块儿石条。一开始我还跟河北那些小年轻儿的拖过几趟石条呢,那真是石条在后头撵着你跑,没两下子的好小伙子都拖不了。”
“那— 出过事儿么?”
“怎么没出过呢!那年有一个大车把式不就出事儿了么:下坡车闸链子崩断了,那么老陡的坡儿,还是重载儿,再好的辕马也坐不住。那老爷子抱着大车辕子不撒开,那能刹住了么!左边儿肋骨折了十一根儿,腿大筋都折了。”
我不禁呆住了:看来赶大车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那他怎么不跳车呀?”
“那前儿老人儿都想不开,大车不是集体财产么,谁都怕有个闪失,人啥样儿不要紧,大车不能毁了。要搁现在谁那么豁命呀,人没事儿才是最要紧的。”
“是,现在都讲究以人为本,生命最贵重。”
过完年天长了不少,却还是黑了下来,三姑和两个孩子回了娘家,家里就剩我们爷俩。院儿里,三姑父关上大门,我挂上里外两层窗帘,进厨房外间往炉子里填上煤。三姑父把外屋门插上,爷俩回屋上炕,三姑父拿遥控器打开52寸的大液晶电视,“小子,我这大电视不赖吧?”
“嗯!这间主卧房也够大,真好!三姑父,爷爷的大鞭— 还有么?”
“有啊,在老院儿搁着呢,明儿天儿要好,我领你上榛子沟你太爷爷那儿拜年去,再上老仟儿顶弄一车大柴火拉回来,咱们爷俩来个原景重现。”
“真的么?那太好了!谢谢三姑父!!!”
“这小子,又鸡—不是外人儿,还谢啥呀?瞅电视吧。”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蓝天万里无云,煦暖的阳光洒满了村庄山野。爷爷的老院儿在村东头儿,三姑父抬手一指,“老院儿本来是石头院墙,头年大队出钱给换成了砖墙,大门也换成铁的了。”大门打开,小园儿花儿墙,上房三间,是旧式儿的瓦房。“大队本来说给换瓦换装修,你大爷一家子都上滦平上班儿去了,也在那儿买楼了。你爷爷走得早,老奶子跟他们一块儿住,这房子也住不着了,我就没换。”
“三姑父,爷爷啥病走的呀?”
“哮喘,老爷子赶了大半辈子大车,大队本来有饲养员儿,你爷爷非得自个儿喂他那仨牲口,按时按点儿上夜草,恨不得跟它们住一块儿。再加上起早贪晚儿,刮风下雨都得出车,就作了那么个病。”
“哦,原来赶大车也这么辛苦!”
东院墙下,三姑父掀开苫布,果然就是那挂大车,因为一直使着,加上保养得好,水曲柳的车辕跟车厢板儿依然泛着光泽,车轱辘也是头年新换的。我忙坐上左前沿子,“嘚,驾!”
三姑父又乐了,“小子,待会儿再练,走上屋,我给你瞅一样儿好东西。”
东间儿屋,三姑父从柜上拿起一个红布卷着的东西,炕上解开绳儿展开红布,里头却是个画轴。三姑父再炕上把画轴打开,是一幅两米多宽、通炕长的大画儿。画儿的背景是冬日的老公山,披着淡淡的白雪,一个头戴狗皮帽身披羊皮袄的长胡子老人两脚叉开站在大车上,大鞭高高扬起,通红通红儿的鞭彩儿仿佛跃动在蓝天雪峰里,非常漂亮。大鞭大车在雪后的阳光下闪着光泽,跟封冻的滦河相互辉映。画右上方一列竖排的行楷:大鞭在握 威震山河 左下角是落款和年月日。杨景晔一看是一九七八年:好嘛,爷爷威震山河前儿还没我呢!
三姑父满脸得意,“这是咱们滦平一个挺有名儿的大画家给你爷爷画的,赫亮吧?”
“嗯!赫亮。”
西屋,三姑父拎着大鞭出来,“小子,拿着,我去借俩骡子去。”我接过大鞭,果然沉甸甸的。爷爷的大鞭可真长,不说三米也有两米七八,大鞭座子也壮,都够我满把攥了,“爷爷这把大鞭可真好,我还以为就东北的把式使大鞭呢,敢情咱们也有。”
“那是,咱们的大鞭比东北有名儿。你爷爷这把大鞭鞭座子是二十多年的水曲柳,自个儿养的大黑狗,金沟屯老白给熟的鞭梢儿,待会儿我教你练练。”
不到十分钟,三姑父就借回来俩骡子,跟自个儿家驾辕的大白马正好儿三套儿。三姑父教我套上大车,把给榛子沟太爷爷带的烟叶大黄米酒等礼品装好,带齐路上的饮喂用具,左前沿子上让我坐在他怀里,我们爷俩共掌大鞭,赶起三套儿大车出了家门。
村外宽阔的柏油公路上,三姑父先教了我不少口诀:赶车全凭一声叫,要不你就喝不醒套。饥不上套,饱不加鞭。不怕千日使,就怕一日累。不怕使十天,就怕猛三鞭。紧赶慢赶,歇歇喘喘;牛靠夜倒,马靠夜草。四角拌到,少喂勤添,饮足清水,适量补盐。有料没料,一天三扫。卸套溜几步,牲口不涨肚……
教完这些赶车饲养的窍门儿,三姑父见大车走得挺稳当,“小子,你练练,我抽一锅儿。”撒开大鞭,盘腿儿坐到里头,装上一锅儿烟抽上了。我立刻觉得大鞭份量陡增,“三姑父,我行么?”
“有啥不行的呀?放开了练练。”
阳光明媚煦暖,公路宽敞平坦,三匹牲口都自觉齐心奋蹄赶路,也不用我加鞭催促。三姑父边抽烟边道:“你爷爷那会儿赶大车上老仟儿拉柴火都当天打来回儿,黑夜两点就从家走。那前儿冬天也冷,我刚给你爷爷跟车练手艺,就找一破被窝往大车上一铺,披着羊皮袄抱着大鞭往上一坐。寻思着冷不了,没承想还没到金沟屯呢,就冻得透心儿凉,爷俩都下来跟着大车跑,暖和暖和。”
我听了忍不住想:以前光觉得端着大鞭赶大车威风,敢情也这么不容易。
沙梁子旧坦克团东,那是有名儿的大陡坡,我把大鞭递过来,“三姑父,这坡儿太陡,你来吧。”三姑父却没接,“别害怕,我教你。”教我把大鞭抱在左小臂,右手攥住辕马小缰绳,“车闸到位,眼睛盯紧,甭怕,头回生,二回熟,多走几趟就好了。”
大车过了滦河沿,到荒地儿村桥头儿,三姑父抬手指指,“这前儿修了油路儿好走了,你爷爷我们那前儿都从山根子那三道弯儿走,三道弯儿这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我立刻想起小时候跟母亲回姥姥家,从那山根子走,道儿也就走一挂马车,崎岖不平,矮的地方路面被滦河水漫上来冻得锃亮,高的地方砬子能有十多米,听母亲说早些年就有个大车把式在那道儿上翻过车,仨牲口都摔死了。
大车出了荒地儿村,三姑父指指山根子地下的大河,“那年冬天我爷爷领着我跟老孙家你大爷爷上来拉柴火,回来前儿满载儿,从冰上走,我走前儿车轱辘就陷进去,没下去多少,我觉着不对,照辕马屁股就是一大鞭,一下就上来了。像那个你大爷爷瞅我陷车了倒绕开那儿呀,他还从那儿走,到那儿就打误了,大轴都下去了。咱们家辕马好呀,你爷爷连那俩骡子都解下来给套你大爷爷车上,我拿大鞭连抽再吆喝,那也不行。冰上牲口搂不住蹄儿呀,你爷爷让你大爷爷拿挖锨铲沙子土垫上,那大三九天冰上也没化,垫多厚也不管事儿,我一看就把坐那破被窝往上一铺,你爷爷也不让我练了,自个儿抄起大鞭,上车把大鞭抡开连抽再吆喝,这才拽上来。”
我忍不住赞叹道:“爷爷那才叫好手艺呢!”三姑父也挺得意,“那是,要不能当大把么。”
西沟,天更蓝了,大河水也更清灵,三姑父道:“你别说,西沟这边儿环境儿就是好,你太爷爷儿子孙子上北京的上北京,上滦平的上滦平,你太爷爷都舍不得走。”
“那是,北京哪有咱们这儿空气好呀,滦平都没有西沟这边儿空气好,这儿水也干净,还没噪声。咱们县文联黄主席给西沟写过一副对联儿我还记着呢:‘宜业宜居生态谷,上风上水西沟乡。’这边儿要好好儿开发开发,准赖不了。”
榛子沟,大山下大河旁的阳坡根儿,阳光下静逸祥和,却只剩三五户人家了。不过家家都是新砖墙,大铁门,家家房子都是红瓦、铝合金玻璃窗装修。三姑父道:“这都是大队出钱给换的,你别看这边儿山沟儿,吃喝儿住行,大米白面小轿车儿,哪样儿都比咱们那边儿好!”
太爷爷接着三姑父的电话,捋着胡子笑呵呵出来,我跟三姑父赶紧下车拜年。一番寒暄,太爷爷抢着接过大鞭,“好重孙子,快给太爷爷摸摸,好几十年没摸大鞭了,想死我了!”太爷爷吆喝着把大车赶进整洁干净的大院儿。我一看太爷爷家也是花墙儿小园儿,水泥打的当院,还有俩花坛,房子前脸儿还镶着瓷砖儿,‘好家伙,这老大院儿,这装修,比上城里住几间钢筋水泥笼子可强多了,要搁我我也舍不得走。’
太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这几年政策好,种地不交公粮,国家还给钱,我还有低保跟养老保险。本来我都没打算给我这几间旧房子换瓦换装修,大队都张罗着给换了,习近平就是不赖!”上前拉着三姑父的手,“孙子,这回来了可得多住几天儿,我给你坐石磨豆腐。”三姑父道:“不了,待会儿我跟小子上山弄几捆儿柴火就回去了。”
“敢!怎么着也得陪我住几天,十五再走。没烧儿啦?”
“没有,这不小子想练练手艺么?我来瞅瞅爷爷,就事儿带带他。”
东屋火炕,太爷爷端来茶水儿烟笸箩,炕桌儿上首儿盘腿儿坐下,一说话儿我才知道敢情太爷爷也姓杨,跟三姑和三姑父两支儿还有我们那一支儿都是同宗同源。
正月晚饭早,太爷爷年轻前儿造过厨,四凉四热八个菜:鸡冻冻儿、猪肚儿、杏仁儿、野鸡肉炒瓜子,炒蒜毫儿、烧茄子、油焖大虾、汆丸子。还有酸菜鱼,还涮羊肉,太爷爷自个儿腌的酸菜,夏秋两季自个儿在滦河钓的鲫鱼,自个儿家养的羊过年杀的,样样儿口味儿纯正,浓香扑鼻!
晚饭后,太爷爷老早的就泡上了自个儿家稻池梗上种的黄豆,爷仨热炕头儿上一倚,大被一盖,抽烟聊天儿,美死了!
第二天,三姑父让我套上大车,出村去拉山泉水。等我们爷俩回来太爷爷已经把小毛驴儿蒙了眼镜套上石磨开始磨豆腐了。
晚上,我终于吃上了传说中的鲇鱼炖豆腐了,山泉水,石磨豆腐,滦河川儿的鲇鱼,唯一遗憾的就是鲇鱼是在冰箱里冻的,太爷爷说要是现从河里抓上来、现开现炖更香,“小子,你夏天再来一趟,太爷爷给你现抓现炖,再领你上山打个狍子去,狍子都是瘦肉儿,拿坛儿一焖,香着呢。”
“哎,哎哎,我肯定来!”
晚饭还没吃完,三姑就来电话了,三姑父明显是个惧内的,“行行行,明儿个早晨就回去。”放下电话,太爷爷就说“孙子,你要没烧儿就拉那垛荆梢,我这儿烧火柴不缺。”
“不不,那哪行啊,爷爷,我真不缺烧儿,就为让小子练练手艺。”
“练手艺不更得满载儿么。小子,来来,太爷爷教你码大车。”
转过天,却下起了雪,三姑父又给三姑打电话,满脸赔笑商量半天,“好好,明儿个我一清早儿就回去,不耽误你排(花)会。行行行,好好好,你放心。”
再转过天,天放了晴儿,早饭后,三姑父早早套好大车,太爷爷教我装了满满一大车荆梢,真有大鞭鞭杆子那么高。太爷爷又给三姑父跟我带上榛子蘑菇和好几样儿山货跟吃不了的猪羊肉等年货儿,“孙子,你们爷俩过两天儿还来,我教我重孙子扶犁杖。”
“得嘞。”三姑父自个儿坐在右前沿子上,让我手端大鞭叉开双脚站稳,“小子,起车。”
“哎!”这两天太爷爷手把手儿教我练大鞭准头儿,练鞭头子的劲,练鞭花儿,还专门儿练了吆喝,这回终于能大显身手了。啪啪— 啪!三个响亮的鞭花儿,大山间都带着回音儿,“嘚!喔喔,喔,嘚。驾!!!”
荒地儿村外,我瞅瞅满载儿的大车,瞅瞅不远处的大河,‘幸好现在修了油路儿,不用再走冰桥,要不这满载儿的大车打了误,不好好儿练几年手艺肯定弄不上来。’又想‘现在家家儿都有电饭锅多用锅儿、煤气灶电磁炉,冬天生炉子,烧炕上自个儿大队山跟自个儿棒地弄点儿荆梢棒秸就足够了,再也不用这么辛苦赶大车从老仟儿往回拉大柴火了。连大车都要淘汰了,要不是三姑父跟他那老哥儿几个爷儿几个舍不得,这挂大车也早没了。’
“三姑父,我说句话你别生气,等再过些年你上岁数儿,就把这挂大车传给我吧,行不?”
三姑父抬起头盯着我瞅了老半天,“那怎么不行呢,小子,你要能把你爷爷这手艺传下去,我跟你爷爷都得好好儿谢谢你呢!来来,我教你上坡儿。”
金沟屯,老公山,阴坡雪还没化多少,也还算得上银装素裹。“吁,吁吁— 吁!三姑父,你掌鞭,我上前边儿给你照张几相。”
蓝天,白雪,老公山,大滦河,如诗如画的美景里,三姑父赶着大车过来:大鞭抡开,鞭花儿比二踢脚炮仗还响;大红鞭彩儿跃动在蓝天白雪里,声声吆喝震荡在群峰大河间,我赶紧连连按下手机……
“大鞭在握,威震山河!”
瞬间化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