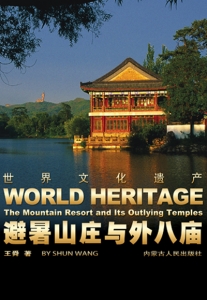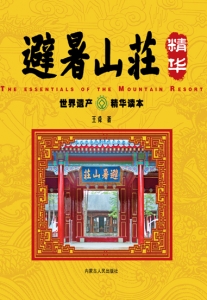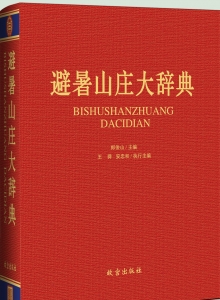李树伟 / 文
(选自:李树伟新浪博客)
什么样的诗是好诗?这种疑问常常在我的脑中回旋。的确,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往往又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不过,好诗毕竟是好诗,它是有着人们公认的道理的。
承德的诗人很多,我特别喜欢:何理、刘兰松、杨林勃、步九江、王舜、李海健、王琦、刘福军、白德成、薛梅、张秀玲、罗士洪、王庆学等诗人的诗,他们的风格通俗易懂,寓意深刻。简单地说,看得懂的诗不一定不好,不一定就是直白,就是无诗味。
看不懂的诗不一定就好,不一定就是含意深刻。这要看诗人是为什么而写,是如何写的。艾青曾说过:“诗好坏,不能以看得懂与看不懂作为衡量的标准;也不能以为人理解的程度作为衡量作品的价值。”我自然赞成这种说法。
虽然,我平时读书并不刻苦,但保持得很好,一直有写感受的习惯,因为上学的时候喜欢读徐志摩、田间、艾青、郭小川等诗人的作品,养成了痴迷诗歌的爱好。那时还真有想当个诗人的理想。觉得诗人是最牛的人,最有水平的人。于是,唐诗宋词玩命地背,喜欢徐志摩等那代诗人的现代诗歌就偷着学,为了提高水平,自然订阅了诗刊。
再后来,不仅不订阅诗刊了,还不爱看现代诗了,更不想当诗人了。文友问我:为什么?我曾经调侃说:如果有掏粪工和诗人这两个职业由我选择的话,我宁愿掏粪去。
我之所以如此厌恶诗歌,不是要标榜自己如何的特立独行,也不是要显摆自己的造诣有多高。
还没走上诗歌的道路呢,能有什么造诣可言?我厌恶现代诗歌是因为它叫人看不懂,是因为它与人民的距离越拉越远。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承德的诗歌界,还有我上面提到的一些诗人,他们还在我的身边,挖空心思地创作。
我这样说,那些喜欢写晦涩的诗人们会不屑一顾的说:“看不懂,是你的水平太差。我们的诗歌精彩着呢!” 让我回答:你们的诗歌究是否精彩,已不能让我这位已沦落为外行的人评说了。但照我个人的感受是没有精彩可言,只是一些汉字奇怪的组合起来而已。
还是让我们以不同风格的两首诗歌为例吧:第一首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我爱这土地》这首诗,难懂吗?它的含意是明朗的。而这首诗又是这样杰出,有着巨大影响。这就清楚表明,含意明朗而又成其为好诗的诗,是要看诗人的艺术工力的。
我们再选一首,就不提这位著名诗人的名讳了,他的一首“《静》坟上生了一株草/蚂蚁咬着命根/栽在地下/欠债的/流血的/月亮看到了”这首诗歌是某文学杂志的精华作品,我实在没看出精华在哪里,也没看明白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诗歌是一种艺术,是要一定的修辞和技巧,否则就是一杯白开水,但现代诗歌,似乎在进行一场猜谜语竞赛。他们写的诗是越晦涩越好,能叫人莫明其妙,就是他们的最高境界。
诗人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出自己的水平,好像时髦诗人、作家,不显现出《丰乳肥臀》就落伍了。我就不明白:就是“照葫芦画瓢”,也得拿个葫芦做样子吧?你那空穴来风般的汉字组合,谁知道你刮的是那股风呀?
时代在进步,诗歌也该与时俱进。但不是这样个进法。真正的与时俱进就该走进人民,走进生活,写出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时代人的生活。而诗人们却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写诗好像做贼一样,躲避着人们,生怕被别人认出来。似乎离人们的生活越远越好。
承德的诗歌界也是一样,他们自成一派,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摇头晃脑,你说我高,我说你妙。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吃了红烧肉,用卫生纸擦了之后,做出一副啥也没吃的清高来。
诗歌是文学的一个种类,是人们文化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怎样发展,衍出多少的流派,终究是写给人们看的。诗歌的本质是具有人性,而不是一意孤行。
你们该清楚:现在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还多。你们每天挖空心思写出来的东西不说没人喝彩,连看的人都没有,这种现象不值得你们反思吗?
不要指责读者不给面子,是看不懂。你们难道是考验人们猜谜语的智力嘛?
别跟我说什么“时空错位”、“审美隐语”等理论,那是你们自己编造出来的,不是人们需要的。你若再整出个“乾坤大挪移”来,我还以为你是打把式卖艺的呢。
我觉得现代诗歌更像巫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是凶是吉,你自己猜去好了。还不如“华南虎事件”中的周猎户呢。尽管是伪造的,但起码还有年画可以参照,总还是纸老虎吧?而你们写的那些诗歌,纸老虎都不是。难得你们还饶有兴趣的写下去。
写到这里,已经很生气了,为了挽救心情,还是回到诗人艾青对于土地之爱上来吧。用他那“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来撼动人心吧。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两句写得朴实平易,却有着惊天动地的撼人力量。因为这“泪水”里,含着多么丰富的情感啊!千言万语,不用说了,一切的一切,都含在这“泪水”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