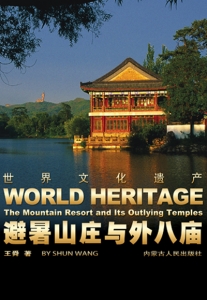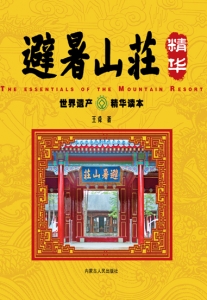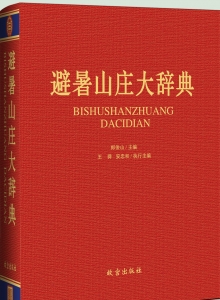后记
出身于工人家庭的我,生长于十年动乱年代。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真是革了文化的命。仿佛就在一夜间,文学名著变毒草,知识分子靠边站。正是嗷嗷待哺、渴求知识的时候,学校缺老师、少教材。今天组织上工厂学工、明天通知下田地学农,后天号召进营房学解放军,就是不系统的安排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过没有关系,那时流行一句话:“学不学都升学,会不会全毕业”,大多数人倒都乐得一个轻松、快乐,玩不够的玩,敞开玩。我以为自己还属于特例,因为没有特别挥霍流金岁月。偷偷地、悄悄地看了一些书。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三国演义》、《红楼梦》、《闪闪的红星》、《我要读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源》、《万山红遍》、《沸腾的群山》、《大刀记》《渔岛怒潮》、《新来的小石柱》以及《十万个为什么》,还算得到过一些文学的熏陶和科普读物的滋养与润泽。
难忘1978年那个烈日炎炎的暑夏,“七月流火”,毒辣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我参加了十年浩劫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数年后被考核、选聘为企业党委办公室秘书。近20年来,大部分时间在单位办公室主任岗位上履职。可以说,文字一直与我有缘,而且从未走远。
也许是上苍的冥冥安排,因为,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依稀记得,用铅笔画字的情景。别的孩子也许是天性使然,都爱画画,在纸上自由涂抹,而我则是像模像样的拿起铅笔,平展展地铺开一张白纸,恭恭敬敬地对着屋子墙上贴着的领袖语录用心描那我心目中神奇、神圣的方块字。它不是作业,不是功课。因为其时,我也还未入小学,也没上什么幼儿园、育红班。尽管那些字,我几乎大都不认识,可是,就喜爱这样做。这样说来,我与文字结缘似乎有些神秘色彩。但细想,还是另有缘由的。应该说慈爱的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他导引我走上了文字之路,使我对文字发生兴趣,喜爱及至痴迷。父亲高大健壮、人品正直、心地善良,虽严厉而不乏舐犊之情。他工作很上进、很勤奋,也很优秀。繁忙工作之余,在家中经常翻阅报纸杂志,我记得的有《参考消息》、《河北日报》、《红旗》杂志、《华北民兵》。那是物质匮乏年代,吃饱穿暖已属不易,零花钱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已属奢望,但也不是没有。每逢节日,父母总还是给个块八角钱的。我就用它上新华书店,买连环画、买样板戏剧本、买新出的各种小册子,有文学的、也有政治、历史、地理的,非常有限的块八角钱全用在了买喜爱的书上了,自然就买不了汽水、雪糕、烧饼以及诸如此类所谓好吃的、好喝的了,但我并无些许憾意,因为拥有了新书,我就像享受了一场豪华精神盛筵,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慰充盈了全身,发散至每个毛孔,极大的满足感全景式地呈现,无法掩饰,并一直陪伴我直到买到下一本新书为止。
其实不是什么前世有缘,我宁可相信是父亲在我幼小的心田植种了文字、文学的种子。我忘不了这样的情景:当年忆苦思甜代表作品《半块银元》,那时极为轰动。在一个冬日的夜晚,饭后,我们一家人围坐炕上,父亲给我们逐字逐句朗读这个故事。现在想来,他当时读的真是极富感染力,可谓声情并茂。听故事的我母亲、我弟弟、我妹妹和我,不由得情动心中,一个个都被故事情节、主人公命运攫住了心灵:或眼里闪着泪光、或泪水腮边挂满、或任泪水滚滚流淌、或仇恨的怒火溢满胸膛——都对主人公王小龙的悲惨遭遇给予了无限同情,对压榨、剥削、残害王小龙的恶霸义愤填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竟萌生了这样的誓愿。我平生第一次体验到了文字的这种神奇的力量。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在文字的道路上蹒跚学步。
拙作《只因有爱》出版了。也算遂了我儿时就怀揣着的一个心愿。苏轼说“春江水暖鸭先知”,其实,我要说“摇笔甘苦我自明”。自然,我不敢说《只因有爱》中的篇章字字珠玑、句句锦绣(其实本就不是这样),也不敢说她的立意多么高远、构思怎样精巧、遣词如何严谨(其实也不是这样,至少不完全是)。但我敢说,它们都是很合乎现代汉语规范的,文章的做法也是可资借鉴的。相信读她有益无害。
现在书是出了,然而我也有些不安,甚而至于惶恐。虽然,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怀着一颗敬畏之心的,但限于水平,疏漏和不当之处恐难避免,期待着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我将以此作为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动力,促我不断成长的养分。
问读者朋友们好。
二〇一二年初夏